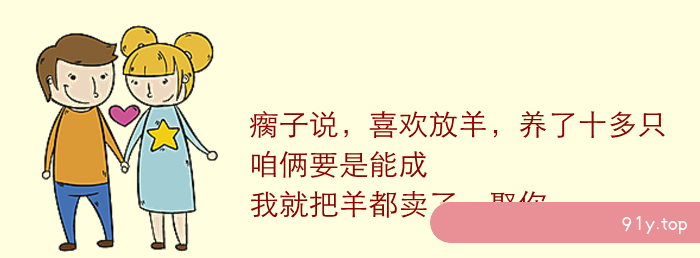好老师可遇难求。
幸运的是,我大学时还就碰到了一位。
这位老师叫叶舒宪。
(叶老师老啦。也是,我们都老啦,叶老师怎么能不老?)
占座位
叶老师当年30刚出头,独身,中文系破格提拔的最年轻的副教授。叶老师的课从不点名,但教室总是座无虚席,经常有外系的慕名前来听课。如果有他的课,我们宿舍如临大敌,占座是对我们最大的挑战。
我们七人排一个班,轮流占座。如果轮到那些习惯睡懒觉的舍友占座,只要闹铃一响,她就毫不迟疑地从床上射起,草草洗漱完毕,拎着晚上早早准备好的七个坐垫就向教室冲去。如果占不上坐,我们能把她给吃了。不但要占上座,还要占好座。公认的最好的座位是第二、三排的中间。至于她的早点,我们会给她带到教室的。
如果叶老师的课被安排在第二节,那我们中就得有一个人牺牲第一节课以保证能占上第二节课的座位。
那时排课也不知怎么考虑的。第一节课在教学一楼上,第二节课就有可能去教学五楼上。中间的20分钟很紧张。
第一节还没下课,负责占座的舍友就抱着几本书或提着我们的坐垫,把着教室的门靠边站着。把边站,这很重要。如果站在最中间,下了课,里边的一出来,就会被挤到一边去。把边站,手可以紧紧抓着门,就没有被挤走的风险了。
有了专门占座的舍友,其他人就从容多了。下了课,先上厕所,再背着书包,逍遥自在地去教室。经过那些满脸焦急、左顾右盼找座位的人身边,我们的得意溢于言表。如果座位占超了,还可以做个顺水人情。那感觉,一个字,爽!
轶事
上一级有个女生号称系花,刚一进校,就在迎新晚会上又唱又跳,大展身手。后来,她在校期间,中文系的晚会主持也让她全包了。相传叶老师带上一级课时,这个女生交的作业就是一封情书。
至于叶老师怎么处理这件事的,大家并不怎么关心,只要那个系花没被接受就行。女生听后,脸上笑笑的,心里却说,幸亏他现在还是单身;男生直接就说了:“生子当如叶舒宪啊!”这绝对没有不敬的充分。
当然这事是一届届传下来的,真实性没人去考证,但大家还是津津乐道。
据说,有同学偶然在系运动会上看到了各项记录的成绩及记录创造者的姓名。中文系撑竿跳的记录保持者竟然是叶老师。这让我们大吃一惊!
叶老师个子不高,印象中一米六五左右吧,一张圆乎乎的娃娃脸。他学问好,没问题;可他体育好,真让我们难以想象。面对他,我们觉得真是高山仰止。吃惊之余,更是增加了敬佩之情。人家这才叫德育体美劳全面发展啊。
西方文学史
“您为什么对我讲这些?她跟您与我无关。您以为我穷,不好看,就没有感情吗?告诉你,如果上帝赐予我财富和美貌,我一定使您难以离开我,就想现在我难以离开您。上帝没有这样,我们的精神是同等的,就像你和我经过坟墓,将同样地站在上帝面前。”
中文系的学生,尤其是女生,哪个背不出《简爱》中的这类句子呢?我们原本以为,勃朗特三姐妹中毫无疑问以写出了《简爱》的夏绿蒂·勃朗特最有名。可是,可是,教《英国文学史》的叶老师完全、彻底地颠覆了我们这一根深蒂固的印象。
(勃朗特三姐妹)
他讲授的艾米丽·勃朗特写的《呼啸山庄》给我们留下了永不磨灭的深刻印记。
听这部分时,我们边听边奋笔疾书,恨不能把叶老师讲的每一句话都记下来,回去后再慢慢消化。下课铃一响,大家不约而同地长舒一口气,放下笔,甩甩酸疼的胳膊,脸上的表情既享受又遗憾。享受当然是指徜徉在《呼啸山庄》的美妙世界了,遗憾的是一节课怎么这么快就过去了?
对我来说,记叶老师的课堂笔记需要两个本。一个本是课堂上的急就章,为了记的尽可能全,就难免写得潦草;另一个本就是课下重新整理的了,整理过程中起码还要借来两本互相参照。
毕业后,我把这本笔记从学校带到了单位,后来又搬了几次家,次次都清理掉一些东西,但这个本子一直保留到了现在。
对了,听完这门课,我们一致觉得《呼啸山庄》远比《简爱》重要。它的艺术成就,它的深刻独到,它在文学史上的地位,都是《简爱》难以企及的。
方言
一同学考到外地大学,写信多次抱怨老师上课用方言,听不懂。过了整整半个学期,才算听明白了当地话,虽然还是只能听不能说。
想起我们大学时的方言问题。现代文学老师是陕西人。一次,一舍友上完现代文学课,拿着自己的笔记向我请教,“而本”是什么意思。我看着这两个字,愣了半天,又想了半天,怎么也不明白。翻开自己的笔记一对照,我忍不住大笑起来,笑得半天都说不出话来。我敢打赌,你绝对猜不到这个“而本”是什么意思。老师在讲到一部作品的背景时,提到了抗战,当然就会提到日本,陕西有些地方把“日”读成“而”。我听的时候不觉得有问题,想不到给外地的同学带来了这么大的困惑。看来推广普通话真是太有必要了。
但就还有人喜欢陕西话。一新疆同学觉得陕西话非常好听,就经常缠着陕西同学说方言,最后竟觉得不过瘾,专门坐公交车听售票员报站。那时由师大开往火车站的是3路车,到了周日,她就坐上3路车到火车站,然后再坐回来。回到宿舍,就学报站,虚心向陕西人请教,不久,她报站的水平,就和陕西籍的售票员不差上下了。到毕业时,她说一口标准的陕西话。过了若干年,她在电话中还能说一口陕西话。
太阳风
虽然上的是师大的中文系,但还是有很多人做过作家的梦。
那时候朦胧诗风靡一时,抄诗成风。我们人手一个厚厚的笔记本,一首一首地抄北岛、舒婷、顾城、江河、杨炼等人的诗歌,用自以为最漂亮的字体,还给配上插图,觉得要保留一辈子的。我们随口就能背出一首首的朦胧诗,卧谈会有时就变成了背诗会。
我们按一定的顺序背诗,后边的人不许重复前边的。轮到谁那儿卡壳了,谁就被淘汰了,最终留下的那一个当然就是冠军了。
单背别人的诗歌明显不过瘾,那就自己动手写吧。开始写的诗还不好意思拿出来,后来就彼此当对方的读者了。有一回,一个舍友通过转弯抹角的关系请来了一个诗人,据说在《诗刊》上发过诗的,现在想来,充其量也就一诗歌爱好者吧,但当时在我们心里就不得了了。我们都想得到诗人的指点,但都没有勇气献丑。推来推去,最终把我们公认的写诗最好的小妹妹推了出来。小妹妹诚惶诚恐地拿出自己的习作,请他指点,我们一个个毕恭毕敬地站着,洗耳恭听。
诗人看了几首,说了一句“这都是病态诗”,我们面面相觑,说不出一个字来。
那天诗人所有的评价好像就是这六个字。
送走诗人,我们先是沉默,后来就开始反驳,最后决定孤芳自赏,出一本我们宿舍的诗集。
说干就干。每个人先自选五首诗,起个笔名,再写一段自我介绍。一舍友的妹妹在美院,专门请她给我们设计了封面,并绞尽脑汁为诗集起了一个名——“太阳风”。然后就是刻蜡板,找关系油印,装订。
(没想到它已沧桑成这般模样)
我们的诗集送出去了一部分,最后每人剩了两本。
这就是那个诗歌梦想给我们留下的唯一印记了。

 素泡屋
素泡屋